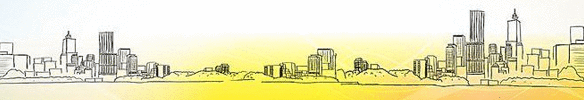记者 |
编辑 |林子人
随着1980年代亚洲经济的发展,华侨、华人研究日益增多——从移民史到文化、社会研究,相关研究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大。进入21世纪后,在全球化趋势下,有关华侨、华人自我认同的研究也开始蓬勃发展。如此背景下,日本历史学家、汉学家、现任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滨下武志开始了他对华侨、华人史的研究。
滨下武志早年东京大学期间师从田中正俊教授,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亚洲经济史。1960年,美国和日本签订《日美新安全保障条约》,促使当时对日本社会议题格外关注的他开始重新思考战后世界及亚洲格局下日本的位置。为了更好地理解近代日本史,滨下尝试了解亚洲不同区域的历史,并在毕业论文中通过对上海机器织布局到棉纱厂的个案分析讨论棉布的历史。在他看来,个案研究不足以支撑对中国史乃至东亚史的全面了解,但这次研究经历使他意识到对中国近代化的讨论应该跳脱出“落后/发达”的二元对立框架。
在后来的著作《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滨下对以往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化时主流的“西方冲击论”提出异议。滨下认为,“以朝贡关系为基础的亚洲区域贸易圈即使到了近代,也规定着西方’进入’和’冲击’的内容。由于西方进入而缔结的各种条约,实质上也正是按朝贡关系中的方式来处理的。”研究生后期,滨下武志加入了东洋文库(时为莫理循文库)的研究计划,大量阅读海关史,了解西方如何看待亚洲,逐渐成长为一名亲亚洲派学者。
打破以往按国别考量地区经济史的传统,以亚洲内部历史脉络为线索,结合实证和理论回应“亚洲之所以成为亚洲”是滨下武志的研究特点。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滨下在参与香港大学亚洲研究所教授景富朗(Frank H. H. King)关于汇丰银行125周年银行史的研究时接触到了汇丰银行的档案馆资料。滨下在整理马来西亚马六甲分行到本行的支票中发现,虽然当时大量的支票来往没有被明指为侨汇,但实际就是侨汇的一种形式。1990至2000年间,更多侨批(专指海外华侨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汇寄至国内的汇款暨家书,是一种信、汇合一的特殊邮传载体)资料开始涌现并被编辑出版,广东及福建省纷纷建立了相关档案馆。此间滨下多次往返于东南亚、华南地区的侨批局,对当地的华侨、印侨移民进行研究调查。2012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这一节点前后,滨下进一步结合以清末海关税务司马士(H. B. Morse)为首所整理的海关资料与国际收支报告,完善其对侨汇、侨批史的历史考察。
2013年,滨下出版了《资本的旅行》一书,这本书以他从197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期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东南亚进行田野调查和资料调查过程中发表的论文为中心,在改定基础上加入新论文出版。书中将东亚及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从亚洲经济圈的视角讨论侨汇与亚洲金融贸易体系的关系,上溯华侨侨汇和朝贡体系及帝国殖民的历史关联,论述了从19世纪后半叶到21世纪华侨、华人金融网络的情况。
侨汇的流动是否是移民地到出发地之间、点到点的单线过程?华侨投资的关系网到底是根植于华侨固有的“民族性”还是国际迁徙带来的“跨地区性”?近日在《资本的旅行》中文版新书发布会上,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副院长冯立军、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席教授燕红忠等嘉宾与滨下武志就上述问题展开了讨论。
何谓亚洲经济圈的“关系网”?
在冯立军看来,滨下武志在华侨经济史研究中融入的跨学科视角是其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虽然经济史是这本书中的考察主体,但滨下在书的开篇几章中引用了“宗族”、“认同”等人类学和社会学概念对其研究的文化背景进行铺垫。譬如书中谈及,就华侨、华人、华裔三代论而言,“华侨”,特指拥有中国国籍的第一代移民,在1960年代前被用来统称以上三种身份。华人实际指二代移民,相比华侨本土化程度更深,对移民地有着更强的归属意识;华裔则是第二代华人进一步移民迁移,其身份认同更少受民族、国籍影响。由于身份认同的差异,三代人在移民地的经济活动也呈现出“维持”、“适应”和“创新”的不同特点。
书中多次出现的“关系网”一词则从社会学中借鉴而来,意在讨论超越家庭内部联系而定位于社会关系网中的“家庭”。这种关系网由人的移动为前提在地区之间形成,不如家庭内部关系那样拥有较强的整体性,状态较为松散。对于“关系网”,滨下自己在自序中做出如下阐释:一是交通概念的关系网,指道路、铁路、航运等,以及各种交通运输工具;二是有关信息交换的关系网——以电信、电话、邮件等手段形成的信息交换关系网在信息化社会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三是物与人移动的关系网,即与物的移动和流动,以及人的移动相关的关系网;四是代表着社会性联系及其转型的关系网。
人、物、钱及信息的流动构成了华侨、华人的移民网络,这也可以视为他们在亚洲的经济活动范围。滨下讨论的亚洲经济圈不一定是国家之间的范围;这个圈可以宏观理解为海洋贸易的范围,也可以具体到城市里一位华商的经营活动网络。以往对于亚洲经济史的研究多按国别分类,将亚洲这一地理空间的各个国家分别进行讨论,其总和则为亚洲经济史。滨下对于“关系网”概念的利用打通了区域经济研究当中国界的壁垒,也为侨汇研究提供了学术理论上的支撑。

[日]滨下武志 著 王珍珍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4
侨汇流通如何推动中国乃至亚洲金融外贸市场的发展?
侨汇的流通或是途径水客、客头;或是通过信局、粮号及银行,这些环节互相连接,形成了一张横跨外汇经营市场和商品市场的金融市场网络。燕红忠强调,在这个过程中,信局并不是收到款项后立刻汇款,而是要集中款项,等到利率比较有利时再进行汇款。在金融市场上,信局利用各地的汇率波动买卖货币、或者利用两地市场的价格差(如新加坡和香港)进行投机,在盈利的同时实现汇款流动,又或者通过货币期货投资来赚取利润。诸如此类的手段都是进入市场的一个很典型的操作,而且非常的现代化。
同时,侨汇网把国际金本位市场和亚洲银本位市场连接起来,成为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在燕红忠看来,侨汇网最大限度地利用了香港的国际金融市场和市场中各种投资、投机的活动,使得资金的流通量极大增加,同时扩大了东亚地区金融市场的覆盖面。
不仅如此,侨汇也是近代中国实现对外贸易顺差补充的一个重要手段。当时的华南地区同时进口金银和货物,流入的资金在近代时期很大地抵消了上海和香港地区产生的对外债务,形成一种相互抵消的平衡关系。从全国范围内来看,1920年代以来每年有数千万年两的白银汇到中国,1920年代超过1亿银元,1930年代超过2亿银元。书中提到的诸多数据都反映出华侨侨汇对当时中国金融市场形成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最后,侨汇在流通过程中直接参与了贸易投资活动。华侨商人不是单纯汇款,而是把如米、砂糖等食品以及手工业原料从海外进口到华南,同时又从中国出口杂货、手工制品和茶叶。华南和东南亚之间于是围绕汕头、香港、曼谷、新加坡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移民贸易和侨汇关系网:香港和新加坡充当了东南亚和华侨出发地之间的中转站,并把这种贸易关系向北延伸,连接到上海、天津、营口和大连,实现亚洲的贸易和金融网络对接。无论是在地区内部还是地区之间,侨汇的流通都为贸易关系网建立了与它相适应的金融关系网,为贸易投资环境的市场提供独特的资金来源。
20世纪初的亚洲金融市场是保守还是灵活?
在中国传统金融体系中,信用的维持多建立在商人与商人之间的熟识关系或是同乡、同族关系之上。各种定期和非现金交易的结算方式都具有中国的文化特色,比如香港、新加坡、潮州之间普遍采用的是定期的结算方式,而不是现金的结算方式。大部分的贸易以30日、60日或者90日为结算期限,有的还累计产品价款进行抵押结算,有的是按年结算,或者根据商品抵达港口的时间来进行定期的交易。在这种信用制度下,华商的生意往来一般只局限于在自家的商号、分号或互相熟悉资本和信用状况的商家——这种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上的、非制度性的结合只有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才能得以维系。也正因此,欧洲商人、企业家或者政府官员长期以来没有开发亚洲金融市场的意愿。在他们看来,亚洲市场具有封闭性强、遵循内部贸易习惯、资金运作以储蓄为主的弊端。
诸如此类的印象使得外界一般认为侨汇的流通在海外华侨与家乡之间具有固定、传统的特征。然而,滨下与他的团队在东南亚做调查时发现那里曾存在金融机构,即侨批局。侨批局创始于19世纪末,在东南亚盛行,它是为取代民信局的汇兑银钱部门而创设的机构,在功能上代替了无组织的水客。中国政府于1934年颁布了取缔民信局的法令,而侨批局得以继续存在,只是必须向邮局登记注册并领取执照。至此侨批局更加积极地向海外发展,业务范围由本来的汇款业务扩展到存款、贷款、信托等方面,与小型银行十分类似。
通过这些机构流转,钱一旦从海外华侨手中离开,其流动就变得非常自由,外国银行也参与其中。在和曾经管理侨批局的相关人士访谈中,滨下了解到华侨、华人的钱不一定从海外直接寄汇至家乡,众多金融机构都参与了中间环节。侨批的钱被用于投资亚洲经济贸易圈中的商品,涉及资源包括锡、橡胶、大米等,如很多来自泰国的大米通过该交易渠道被运送至广州和香港。因此,虽然由侨汇形成的金融网在底层是较为固定和传统的,在这之上有着非常活跃和国际性的金融活动以及商贸关系,为上层提供了丰富而灵活的资金流动。
参考资料
(日)滨下武志.资本的旅行[M].王珍珍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4
(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M].朱萌贵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
https://www.haijiaoshi.com/archives/5193